今年是故宮出版社建社40周年和《紫禁城》雜志創刊43周年。作為故宮出版社第一批作者之一,感覺應寫點紀念文字。但本人為故宮普通學者,難有宏觀上的把握,寫點創建時我親歷的一些人和事,或能留下些感性認識。這些基本上都是圍繞出版社創建人和《紫禁城》雜志第一任主編劉北汜先生的。
一、給劉北汜當助手

劉北汜先生在工作
1978年春夏某日,我從業務部工藝組調至院里重新組建的研究室中的宮廷史研究小組。報到后,主任吳空說,研究室重組,要從各部門調些人馬。現在宮廷史組的人員還沒最后確定,這段時間可先協助劉北汜做《院刊》編輯工作。吳空告訴我,劉北汜是《大公報》老記者老編輯,抗美援朝時作為戰地記者還去過朝鮮,現在不但是《院刊》主編,也是研究室副主任。他把我帶到劉北汜的辦公室,也即《故宮博物院院刊》編輯部, 跟坐在西屋南窗辦公桌前的一位男士打招呼:“老劉,這是調來參加宮廷史組的劉潞。他們組人員還沒配齊,讓她先給你幫忙吧!”被稱作“老劉”的男士站起來跟我握手,說:“我是劉北汜。”我一看,是位又高又胖,戴著那個時代常見的黑框眼鏡的學者。老劉(那個年代,一般都不稱官銜。像我這類30上下歲的年輕人,對年長者會在他們姓氏前加個“老”字以示尊重。)大概六十出頭,跟我說,你在東屋吧,其實這三間房早已被打通,所謂“東屋”,實際上就是東側。我的辦公桌就在東側南窗下。就這樣,我開始了給劉北汜當助手的工作。他見我無所適是,就拿了一篇稿子,說你先看看這篇,有什么問題提出來。對此我表示了疑惑,他說,不要緊,你先認真讀三遍,感覺不順的地方標出來給我。這是一篇標題為《蒸熏器》的稿子,是講故宮所藏治療鼻咽喉疾病的一種治療器具。說一般鼻咽喉炎,將煮沸的相應中藥湯倒入器中,藥湯的蒸汽通過蒸熏器的長出氣管進入患者口鼻,數次就會有所緩解。我認真地把稿子讀了三四遍,標上了有疑問的地方交給老劉。他看過后表示不錯,又遞我一沓稿子,說你再看看這篇,不急,慢慢看。這篇是陳列部副主任楊伯達寫的《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蒸熏器》那篇加上圖也不過兩千多字,內容也不難懂,所以看得快,楊伯達這篇好長,光稿紙就有四、五十頁!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通讀了幾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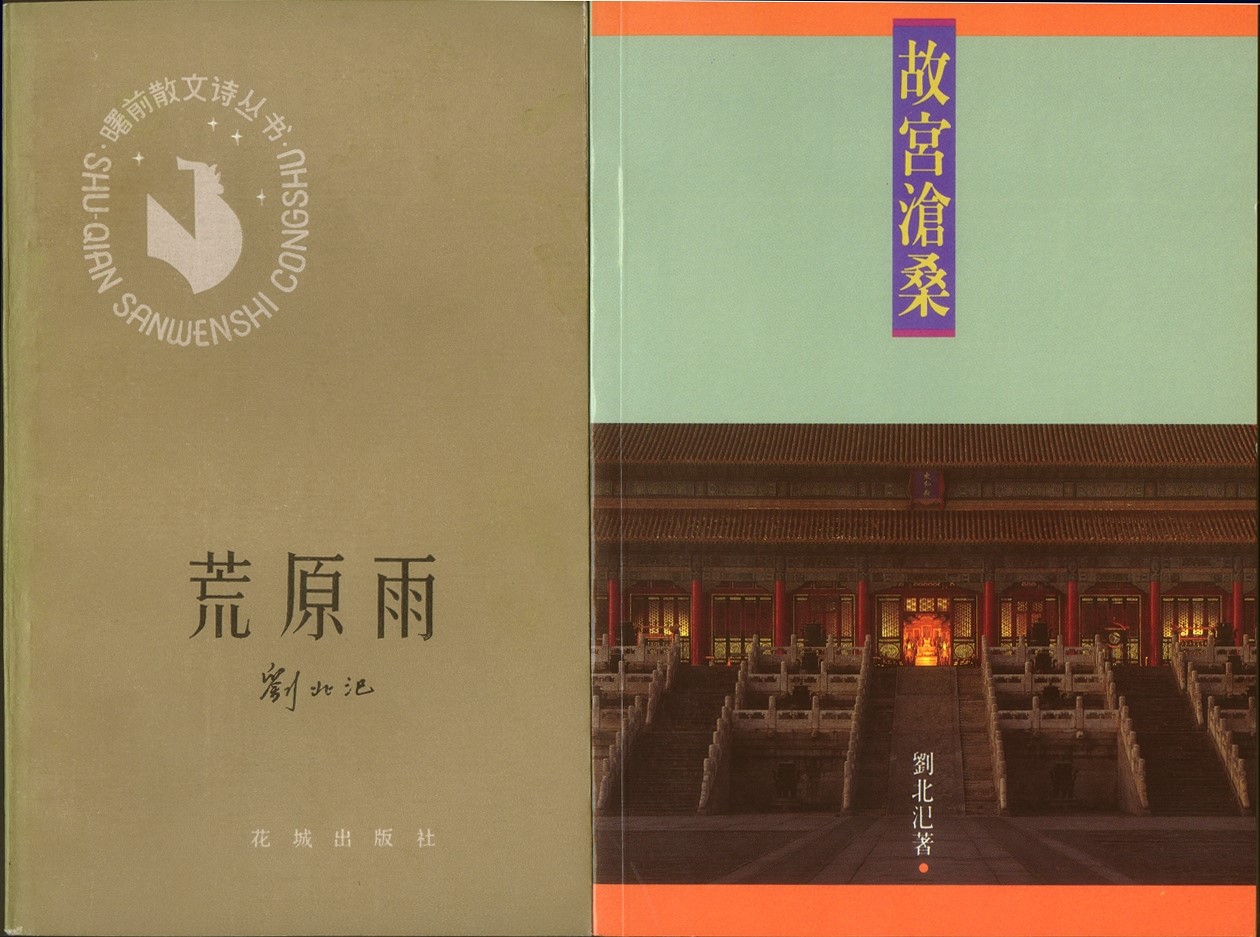
為寫這篇回憶,我特地找出1979年《院刊》復刊后發在第一期的楊伯達的文章,仔細閱讀。這篇文章涉及清宮畫家冷枚的師承、在畫院的經歷、與清帝的關系以及避暑山莊三十六景演進歷史與狀貌。作為一篇研究繪畫的文章,還討論了冷枚是如何在采用西方透視法的基礎上,又依主題需求,調整了畫面建筑的大小,以及通過分辨冷枚不同時期的簽字等,論證是圖產生的具體年份等。時隔40余年,重讀此文,感到無論是內容還是研究方法,都是一篇難得的佳作。現在也記不清我花了多長時間才把稿子退回老劉的了,總之從中學習了很多。我突然悟出,當年老劉讓我看此文,應不僅僅是讓我學編輯,更多地是讓我從中學習宮廷史吧!不過當時我并未將此文作為我學習和研究宮廷史的入門文獻,但奇怪的是,文中講的一些內容,如康熙對科技的熱愛,焦秉貞的經歷與繪畫,都成了我日后研究的重要對象。現在回想起來,真有些不可思議!
每天與劉北汜共處一室,很快就發現,他只要一坐到辦公桌前,除了看稿子,就幾乎不離椅子了。每天中午,也常常是最后一個去食堂,有時去晚了買不到飯,就以方便面解決問題。這樣的工作方式,那時我是完全不理解也接受不了的。我勸他:“老劉,你坐下來就不動,肩背不痛嗎?活動活動吧!”他笑笑說;“沒事,習慣了!”印象中老劉唯有的一次上班時起來活動,還是因要了解一篇寫御花園石子甬路的文章,而叫上我一起去了趟御花園。過了一段時間,宮廷史小組的人員配齊了,我也就不再給老劉當助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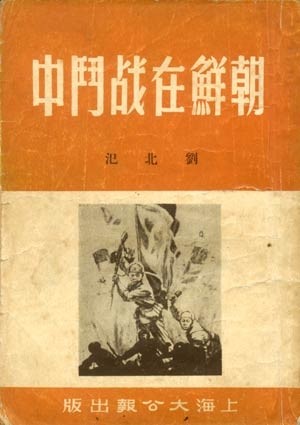
我對老劉有了深入一些的了解,一是他曾是一名入朝戰地記者,經歷過戰火的洗禮,1979年研究室支部發展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員。在支部會上,他詳述了自己的經歷,多數都記不得了,但有兩點卻是終生難忘。一是他擔任過《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二是老劉為吉林延邊人,中學同學中有大名鼎鼎的金日成,中學老師是歷史學家尚鉞。而尚先生在華北大學時是跟我父親過從甚密的同事。好像就這兩點,讓我對老劉增加了不少親近感。

1951年金日成會見上海記者組,(右二)為劉北汜
二、劉北汜對我研究清宮史的直接幫助
第二年,根據宮廷史組的分工,我開始研究順治皇帝的婚姻。從文獻得知他先后有三位皇后,前兩位不是被廢就是長期受冷落,第三位是死后被追封為端敬皇后的董鄂氏。她身上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清初就有傳說她是被豫親王從南京掠到宮中的江南名妓董小宛,后得順治皇帝寵幸。孟森先生在民國初年特別寫了《董小宛考》,但并未考出董小宛是否就是董鄂氏。我決定把這位傳奇皇后搞清楚。前后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終于弄清楚董鄂氏實為順治帝弟襄親王之妃及其入宮的經過,并寫了篇《董鄂妃與董小宛》,去找劉北汜請教。由于稿子不長,也就兩千字左右,他很快就看完了,說,還不錯,放在這兒吧。沒有想到,轉過年,即1980年《院刊》第一期就發表了。更沒有想到,這篇小文還被當年的《新華文摘》轉載。這對初入清宮史研究之門的我來說,不啻是個極大的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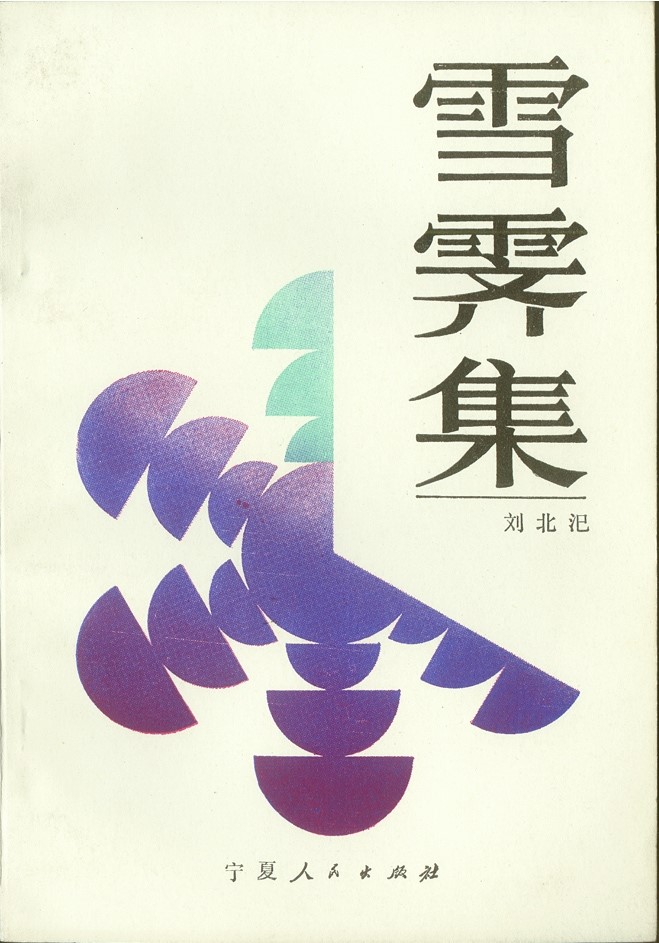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對故宮學術發展有積極意義之事。1980年某日,晚清名臣光緒皇帝之師翁同龢五世孫收藏家翁萬戈來故宮訪問。聽吳空說,翁先生看到故宮百萬收藏卻遲遲沒有條件面世,很是遺憾,表示愿同故宮合編一本以知識性、趣味性為主的普及性刊物《紫禁城》,以向世人介紹故宮的歷史和藏品,他可以在香港做投資方。吳空也表示由于《故宮博物院院刊》已是正式刊物,編輯和作者都是現成的,其它還需要的條件,他在這邊努力。對此同組的萬依透露,吳空雖長期在國務院秘書局工作,但與翁先生頗投緣,乃因其父韓慎先(別號夏山樓主)亦為著名文物收藏家和鑒賞家有關。吳空自幼受家庭熏陶,對古典文史器物有著濃厚興趣。在吳空的大力推動下,此事很快辦成了。《紫禁城》主編為劉北汜,又從工藝組調來了汪萊茵任專職編輯,當年《紫禁城》雜志第一期就出版了。或許老劉為突顯雜志的趣味性,將我那篇《董鄂妃與董小宛》也收錄其中,只是改了標題《董小宛何曾進過宮》。這樣我也就成了《紫禁城》雜志創刊號作者之一。
三、劉北汜助我成為故宮出版社第一批作者
這期間研究室副主任劉北汜和支部書記萬依為加快故宮學術水平的提升,力主在兩個刊物的基礎上成立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社很快獲批成立,劉北汜出任總編輯。當時我在科學院圖書館結識了安慶師院中文系的退休教授邱良任老先生,他來科圖是為研究歷代宮詞而查閱資料。他得知我在故宮研究清宮史時,便跟我說他查到很多清代宮詞,讓我看看。關于清宮詞,以前只讀過王湘綺的《圓明園詞》,覺得寫盡了圓明園的劫難和國運的衰敗,十分悲愴,并不知還有他人寫清代宮詞。邱老說他查到很多清宮詞,我很高興,從他桌上抱過來一摞書,一冊冊翻看起來。有《清史稿》纂修官吳士鑒的《清宮詞》84首、清末御史民初國務院秘書長夏仁虎的《清宮詞》二卷200首、《芋園叢書》中大荒道人黃榮康《清宮詞本事》一卷100首、《清朝野史大觀》中無名氏《前清宮詞》100首、王湘綺高足胡延的《長安宮詞》100首、明末清初張煌言《建夷宮詞》10首等。全部翻完后,我決定去找劉北汜,看看如何利用這些清宮詞。或許清宮詞觸動了老劉的文學細胞,他笑著對我說,這些清宮詞很好啊,既是詩又是史,對你研究清宮史肯定有用。你把它編出來吧!老劉又問了我詩的內容,說這么多首詩,出自不同作者,按作者名錄編排沒什么意思,還是按詩的內容編排比較好。他這一句話點撥了我:首先要認真讀宮詞,再在對內容理解的基礎上將它們分類。于是我按照他的意見開始認真讀原文,進行分類編輯。我將它們分成“人物與事件、制度、皇帝起居、后妃宮女起居、皇子皇女、時令習俗娛樂、珍玩書畫、宮殿衙署園囿、長安宮詞與建夷宮詞”十類。最后,選了三百零二首,并為每首做了注,又請邱老寫了長篇序言。我把成果交給劉北汜后,問他這本書在哪兒出版?他告我準備把它列入《紫禁城叢書》第一輯。1985年,《清宮詞選》作為《紫禁城叢書》之一出版了。版權頁上印有“責任編輯:馮荒,裝幀設計:方振寧,插圖:吳建群”。拿到書后我很激動,我知道馮荒是劉北汜的筆名,他親任此書責編,那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此后,忙于研究編寫《清代宮廷史》,與出版社和劉北汜就沒有那么多直接深入接觸了。1995年他病重住院,我和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秦國經先生前去探望。他已很虛弱,見到我們很高興,強打起精神,講了他做的一個夢:我夢見躺在這床上,身上蓋的不是被子,而是厚厚的稿子。我一聽,眼淚止不住往下流。面對一位給予我諸多幫助的病危長者,真不知能說什么。我哽咽著安慰了他一會兒,又跟他講了一陣故宮的現狀,便跟秦國經離開醫院。不久,他就離世了,享年78歲。
劉北汜先生學識廣博,為人寬厚,不圖名利,兢兢業業,提攜后輩,為他人做了一輩子嫁衣。通過《故宮博物院院刊》、《紫禁城》雜志和紫禁城出版社,為故宮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學者,是故宮博物院和故宮出版社歷史上難得的優秀共產黨人!
謹以此文表達對故宮出版社成立40周年的祝賀,及對老出版人劉北汜先生的敬意。



 圖書館
圖書館
 視聽館
視聽館
 故宮旗艦店
故宮旗艦店
 全景故宮
全景故宮
 v故宮
v故宮













